 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docx
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docx
《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docx(17页珍藏版)》请在课桌文档上搜索。
1、中国性与“台湾经验”评詹姆斯乌登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ChinaandTaiwanEXPerienCe:JameSUdden,sNoOneisIsolatediHowHouXiaoxian,sFilmWorld作者:陈林侠作者简介:陈林侠,中山大学中文系原文出处:文艺研究(京)2015年第201511期第152T60页期刊名称:影视艺术复印期号:2016年Ol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重要的学术方法。在此背景下,海外电影研究很少局限于文本的艺术性,而越来越强调电影作为社会文本、文化文本的属性,重新回到了宏观的外围研究。侯孝贤电影因敏感的政治议题、突出的美学形式,
2、成为文化研究的最佳文本之一。美国电影学者詹姆斯乌登的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黄文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以下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标注页码)是近年的新作,表现出较强的专业性和理论深度。正如作者所说:“这本专著的目的,不仅是提供一个侯孝贤直至今日的创作生涯的概括,而且试图解释它为什么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呈现的大量原因。(第14-15页)他不愿意归纳侯孝贤特有的美学方式,更不打算概括他的创作历程,而是要解释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侯孝贤的大量原因。这揭示了詹姆斯乌登的学术雄心。从作者介绍得知,他为了写作该书,长期居住台湾,并多次采访导演及其合作者。确实,该专著提供了访谈侯孝贤及相关人员的第一手材
3、料、香港学者的英文研究资料,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整理电影文本及镜头语言、镜头时数等重要数据,鲜活的经验、异域的学术理论及其方法,对国内侯孝贤乃至华语电影研究来说,都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乌登的论著虽然存在镜头数量、长度的定量研究(文本内部的形式研究,这种研究方法被译者赞许推崇),但就篇幅与价值倾向看,仍然属于文本外部的文化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电影的文化政治学研究。最明显的标志是:该论著的核心议题在于否定侯孝贤电影被中外学界公认的中国性,而极力强调所谓的台湾经验。对于这一话题的特殊意义,作者有着明确的认识:这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学究式问题,而是充满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的意涵(第296页)。在我看
4、来,这种囿于特殊倾向与立场的文化政治研究,导致了一系列的缺点,如限制了对侯孝贤电影其他论题的挖掘;在具体行文中,首尾处纠缠于非/反中国性的台湾经验,主体论述却时常与这一核心议题错位,等等。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清理该论著关于侯孝贤及其台湾电影史料的缺陷,而是认为,这种细节真实与整体谬误的文化政治学研究,在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辨与反思。一、台湾经验:非/反中国性的文化政治在台湾文学及其电影研究中,台湾经验并不构成比地域经验更高阶的中国文化概念,相反,它以非此即彼的姿态表明自身的政治立场。因此,这种特殊的内涵根本不同于地域文学艺术研究通常所谓的“在地经验(IoCalex
5、perience).它根源于台湾民主运动,是一个为了争取政治独立与国际地位而生造出来的文化概念,存在显见的非/反中国性的政治内涵。乌登对侯孝贤电影的台湾经验研究也遵循这一基本的构架。一方面,他坚决否认侯孝贤电影的中国性:”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如果说中国文化对侯孝贤电影有任可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也在于中国文化在台湾约从1947年(和更早)到今天是如何过时的(第11页)。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台湾对侯孝贤的决定性作用。离开台湾,侯孝贤的电影就是不可想象的(第11-12页)。最重要的,本书试图表明在侯孝贤的创作生涯中,台湾是多么的不可或缺(第15页)。侯与台湾岛是不可分割的,没有彼此
6、不可想象(第345页)。在这种两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侯孝贤电影的政治意义陡然倍增:说侯孝贤作品具有中国性,就意味着否定他的台湾经验;具有台湾经验,就意味着他反中国性的特征。面对“如果我们问影评人和学者,谁是今日世界最中国的导演,毫无疑问侯的名字会经常跳出来(第295页)。这样一个海内外学界公认的结论,乌登采用了几近全盘否定的方式(他相对推崇香港学者叶月瑜的侯孝贤电影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后者的华语电影研究也存在非/反中国性的学术取向)。他首先否定戈弗雷(GodfreyCheshire).傅东(Jean-MiCheIFrOdon)、班文干(JaCqUeSPim叩aneau)、波德维尔(DaVid
7、BOrdWHl)等海外学界那些肯定侯孝贤与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其中也包括乌登自己之前认为侯孝贤的历史态度与艺术直觉都非常中国化”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都是文化本质主义渗透后的大同小异的论述(第2-3页),凡是从总括性解释文化通常是肤浅的(第14页)。继而,乌登也否定中国大陆学界的侯孝贤研究,因为后者总抱有不同的政治动机,有意无意地与官方政策相吻合,研究侯孝贤意味着提倡大中华”的概念,因而存在宣扬民族主义的假定。如针对倪震提出侯孝贤电影表达了儒家精神,他认为:这种陈述并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单纯,事实上包含了一些政治性的弦外之音(第7页)。对台湾学界的侯孝贤研究,乌登也不尽然认同。如在他看来,台湾著名
8、电影人焦雄屏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侯孝贤,只不过是因为她肩负向海外推介台湾电影的使命,从市场的角度吊胃口。退一步说,如果她真的信任侯氏的中国性,那么充其量只是一种偏颇的解释而已(第12页),也就不值得重视。乌登发挥了侯孝贤长期合作者、编剧朱天文的看法(朱认为,考虑到中国文化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之处,把侯的风格界定为中国的,是非常困难的),这使侯孝贤与中国性偏得更远(第12页)。该书的引注表明,这是朱天文接受乌登采访时的论断。我们姑且不论那是否是成熟的表达,单就此而言,她也没有否认侯孝贤风格与中国性的关联,而是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矛盾处,所以将侯孝贤界定为中国的非常困难。甚至侯孝贤自己的说法也
9、被乌登推翻。如侯孝贤在多个场合宣称自己既有中国人的文化因素,也是台湾导演的身份(第12-13页)。乌登的解释是,这似乎体现了侯孝贤受访时的灵活性。那么,乌登是怎样从理论上反驳侯孝贤的中国性的呢?主要有两个层面:(一)历史文化的外围研究。他提出,认为侯孝贤电影具有“中国风格”的研究,就是暗中假定一种本质的、统一的、共时的观念(第8页),直接为之扣上了本质主义的帽子。然后,他以中国文化处于发展变化中为由,认为这个概念是空洞的。中国文化及其儒家传统存在前汉/后汉、佛教引入、南/北、高雅/大众等众多差异。儒家思想在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只是一种思想混合体的组成部分(第8页),从汉朝到隋朝建立遭遇了道教
10、复兴与佛教涌入的围攻。他用道家文化对中国书法、山水诗、画等影响,描述中国艺术传统的多样性。他离题描述了中国思想与艺术的简短历史,目的很简单:只不过为了说明,说侯孝贤的电影很中国,等于什么也没说(第11页)。也就是说,乌登用中国文化存在发展、儒家文化吸纳其他学派思想等理由,轻松地否认了具有本质规定性的中国性。(二)电影文本的内部研究。乌登在描述完侯孝贤创作经历后,更在第四章专辟一节来总结侯孝贤电影不具中国性。其理由如下:1.长镜头不是中国电影传统,因此不能证明侯孝贤的中国性。在整个电影史上长镜头运用得比较广泛,不但在欧洲的艺术电影中,甚至罕见地出现在最近的好莱坞影片(第296页)。2.侯孝贤电影
11、的场面调度强调复杂的立体视觉,布光与日俱增的大胆,然而,中国电影的场面调度相对扁平,布光”缺乏明暗对照(第298页)。3.远距、吃饭等场景、抒情诗意大过于叙事等特征,也难以成为侯孝贤中国性的证据,因为他在后期创作中(如海上花)改变了远距长镜头,而且也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解释大量吃饭场景,所谓的抒情诗意在世界影坛上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第299-300页)。4.认为侯孝贤电影具有中国性,意味着”在文化上不够特别,反而取消他的独特性,降氐了艺术价值(第300页)。我们认为,对于侯孝贤电影非/反中国性的论题,乌登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从写作体例来看,无人是孤岛的外部/历史语境的阐释与内部/文本故事的分裂是明
12、显的。在诸多的文本细节上,很难避免侯孝贤电影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大陆存在着割舍不断的关联事实,如童年往事对广东梅县的乡愁、悲情城市潜在的大陆形象、好男好女中回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情节、海上花的地点发生在上海租界,等等。为了证明台湾比大陆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他认为台湾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想想本土宗教在台湾的复兴,也想想台湾保存了多少在大陆文革中已经丧失的传统文化,很多人认识到,过去的大部分仍是台湾今天的一部分(第345页)。既然台湾保存如此多的传统文化,那么,又怎能认为台湾经验是如此的非/反中国性、以至于两者敌对(第343页)?因此,无论他怎样分辩说外省人第二代的乡愁荡然无存(如童年往事),
13、或仅仅是想象的文化中国(如海上花),还是来自大陆/外省人的压迫(如悲情城市),在侯孝贤的创作中包含如此复杂情绪的中国形象,已然清晰地表明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血脉命运的关联。就他以发展变动为由否认中国文化”概念来说,同样是论证不足。从哲学上说,任何一个事物、现象、观念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使它成为自己的存在,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肯定的否定辩证,产生出黑格尔意义上的生气贯注的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它之所以仍然是其所是,就是因为存在某种难以改变的内在规定性。中国性同样如此。一方面它确实存在复杂的差异性,在传统/现代、本/全球、现实/理想等不同维度之间充满张力,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性始
14、终受制于内在的规定性,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概念。侯孝贤具有中国性,并不意味着他成为同一、本质、僵化的中国性的表征,而是说,他以某种差异性的文化经验、美学形式(道家文化及其美学形式),丰富、补充了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中国性。乌登从内部的文本研究得出的非中国性,更缺乏足够的学理性。我们以长镜头语言为例。他从电影语言(如长镜头、景深构图、富有层次的布光等)具有世界共性的角度来证明侯孝贤电影与中国艺术传统相悖逆,因而并不存在中国性。我们知道,电影语言与自然语言不同。自然语言作为族群、地域、民族、国家等的天然屏障,能够区分文化的他者;电影语言是一种次生性语言,建立在光学镜头、剪辑、冲印等媒介技术基础上
15、,长镜头、场面调度、景深镜头、蒙太奇、剪辑等意义表征,是在西方电影(包括欧洲艺术电影和美国商业电影)大量实践中逐渐约定俗成,并在新的媒介技术支持下,不断出现新的语言形式,呈现出开放的未完成状态。换句话说,电影语言是以现代影视技术为前提,人类共同参与、到目前仍然在不断挖掘开发的功能性语言,它根本就没有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标识具体族裔、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不可能因正反打镜头、平行蒙太奇在美国电影中确立,就认为凡是使用这种镜头语言的均是美国电影。不仅如此,电影作为西方舶来品,是在欧美现代性语境中发展并丰富起来的,而非中国传统艺术之一种,因此中国电影缺乏中国书法、山水画、文人画等那样足以区分他者、标识中
16、国身份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影语言缺乏特殊的内涵,也不意味着中国电影理当没有自身的表征符号。文化研究揭示出语言、言语、话语的区别,即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言语),出现福柯所说的可个体化?口被调节的实践”的话语。语言媒介不仅能够指涉客观事实,同时也具有表现特殊情感效果的功能,这种特殊效果产生于话语的个体实践。也就是说,镜头剪辑、长镜头、静止镜头、全景镜头等构成抽象的电影语言体系,然而,一旦具体到电影作品,在导演的操作实践中就成为特殊的言语。任何一个导演使用长镜头等抽象语言,都是已被调整后的个体化实践。正如乌登概括的那样,沟口健二、安哲罗普洛斯、杨索、张艺谋、贾樟柯、洪尚秀等都大量使
17、用长镜头,但是,此长镜头非彼长镜头,任何导演的长镜头使用均存在自身的独特性。每一个镜头的意义不仅关涉长短、运动、节奏、距离、构图等视觉层面,更取决于拍摄对象、演员表演及其由此传达的意义、情韵、价值等。与自然语言的能指、所指存在相对固定的关系相比,镜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更具自由性、特殊性。个人一旦使用某种镜头语言,不仅与理想中作为抽象规则的语言形态存在差异,也区别于他人的话语使用。因此,长镜头只是镜头形式的概括,并不能说明镜头所呈现的内容。不同导演使用长镜头呈现不同内容,这种质的区分不能被镜头语言的同一名称所抹煞。我们不可能说,张艺谋使用长镜头拍摄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与贾樟柯使用长镜头拍摄
18、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等,就等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戏梦人生、海上花。试想,如果真如乌登所说,他所列举的前三个理由岂不是从语言的共性彻底取消了侯孝贤的独特性?不仅侯孝贤没有独特性,任何导演都没有独特性,欧洲艺术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也没有区别,因为所使用的镜头语言都能在其他导演及作品中找到。这种论断岂不荒谬?二、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虽然对侯孝贤作品作如此政治学分析,乌登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便在悲情城市这样明确表现二二八”事件的文本中,侯孝贤也常常因为他的政治矛盾和逃避而受到统派和独派的双方批评,甚至很少有人能够指出侯孝贤在台湾真实的政治光谱中的位置(第31页)。我们认为,现实中截然对立的统独双方
19、均指责侯孝贤回避政治,这是由于文本虽然表现了政治事件,却又缺乏确凿的政治立场、态度所致。他既不是统派传声筒,也不是独派的鼓吹者,这正是侯孝贤遵循艺术本体性的结果:进入文本的政治已不是现实的政治,它不过是一种经由艺术过滤、体现艺术原则的情绪与气质。可以肯定地说,电影艺术以个体形态、日常生活表现出的微观政治,根本有别于宏观的政治立场或态度,存在着混沌的多义性。关于宏观与微观两种政治形态,衣俊卿作了如此区分: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如果说政治的核心是权
20、力和控制,那么:(一)微观政治意味着权力和控制从国家权力机器、社会机制更深刻地演进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人的社会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它是一种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就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主宰和被主宰、主人和奴隶这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辩证的。但凡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存在控制和被控制等权力关系,就是微观政治所在。因此,电影等大众/社会文本在微观政治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不仅侯孝贤电影挟带了复杂的微观政治意义,李安、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等华语电影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也存在广阔的阐释空间。但客观地说,相对李安研究之于离散批评与后民族主义批评、张艺谋研究之于后殖民批评与东方主义等研究的丰厚程度,侯孝
21、贤及其电影研究仍嫌薄弱。这与侯孝贤及其整个台湾电影研究长期依赖并受限于宏观政治话语及其思路有密切关系,质言之,它尚未进入文本的微观政治学研究。侯孝贤在论述自身创作的“沈从文情结”以及文本中广泛存在的生活现象、中国想象、政治事件及黑帮时,很容易成为统派、独派等生拉硬扯维护自我利益的注脚,乌登的侯孝贤研究也不例外。最明显的例证是,他所推崇的侯孝贤的世界观、云块剪辑法、自然观等,并没有得到系统的阐释,尽管他已经认识到戏梦人生它起落流动的自在,它始终如一的静止,是最节制然而也最深刻的哲学表述之一(第235页)。因为如果再深入下去,侯孝贤和他的电影就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及其美学精神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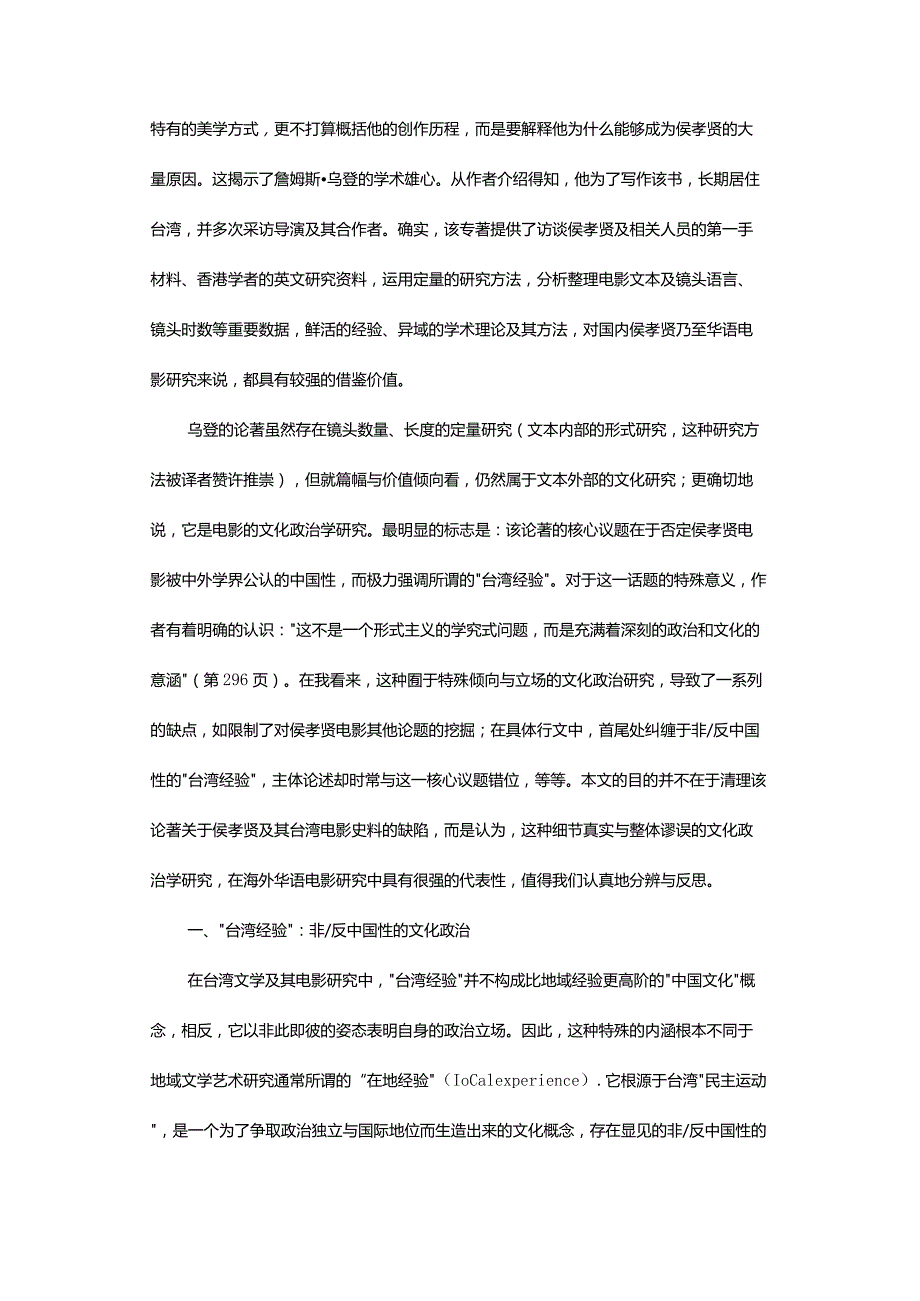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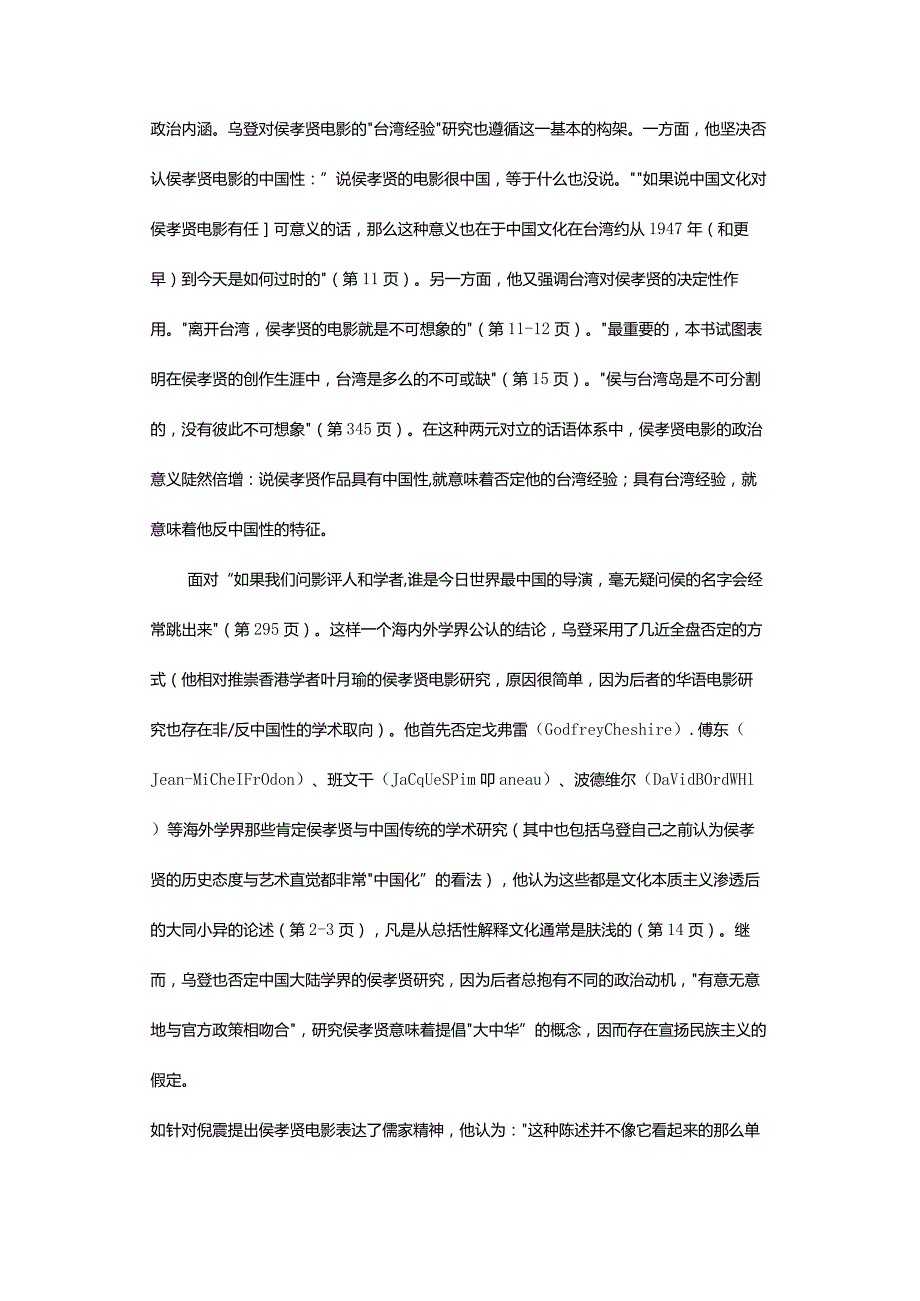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无人是孤岛:侯孝贤的电影世界 中国 台湾 经验 詹姆斯 无人 孤岛 侯孝贤 电影 世界
 课桌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课桌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链接地址:https://www.desk33.com/p-10770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