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docx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docx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docx(24页珍藏版)》请在课桌文档上搜索。
1、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摘要: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判”应为尚书都省誉写的礼部呈录文。其所录省劄的正文并无“奉圣旨”或与之类似的文字,这是金朝后期尚书都省肆意以省劄指挥政务的表现。这反映了宣宗初年宰执施政空间的扩大和对皇权行使的牵制。大金德运图说所载尚书省议”的性质类似于尚书都省的存档备查文书。从大金德运图说所录诸文来看,金朝后期中枢政令的下达渠道有皇帝颁发圣旨和尚书都省下发省劄,以及执行政务的主管机构发送相应的政令文书、官员通过所属或主管机构的公开榜文接到政令等多种途径。皇权对政务的最终决策通过行文格式得到认可,同时金朝后期宰执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仍然存在。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2、和架空皇权,但是的确限制了皇权的向下延伸。关键词:大金德运图说;省劄;文书;中枢政务文书是政务处理的主要载体,以文书为线索研究中国古代王朝社会的政务运行机制,已成为学界的主要研究方式。相较其他时期,关于金朝政务运作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这固然是受制于传世史料的匮乏和记载的缺陷,但同时也是由于部分史籍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新审视所致。其中,大金德运图说就是一份珍贵的金朝后期政务文书。学界以往主要是用大金德运图说讨论金朝德运的相关问题,然而,其价值并不局限于此,其还为研究金朝后期政务文书的文体格式等问题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支撑。因而,本文力图通过对大金德运图说的重新考察,明晰金朝后期中枢日常政务处理的各类中
3、枢机构的层级关系和政务运作实态,以求教于方家。一、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省判”辨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省判”是其所录的第一份政务文书。因被列为诸案牍之首,故此份文书的性质和内容对后续所录案牍有提纲挈领之效,我们首先对此“省判”做一考辨。“判”作为中国古代王朝社会中带有裁决作用的应用文书,自西周出现以来,来因:我国法律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一一西周青铜器“朕画”铭文,法学杂志,1981年第2期。至唐代进入繁盛时期。唐代判文大致分为三种:案判、拟判和杂判。其中,案判又作实判,主要指官员在处理案件或政务活动中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写的判文。谭淑娟:唐代判体文研究,齐鲁书社2014年版,第34页。金朝制度仿自盛唐,金朝
4、建立后,金朝人认为“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金朝的制度架构,取法盛唐之制。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三引王绘绍兴甲寅通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7页。在日常政务处理中,各级官僚机构同样常以“案判”作为政务处理结果的文书。这种现象早在金朝进入中原之初就已经出现。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载,“申覆元帅府并行台尚书省照睑讫却,奉上畔”。此“畔”即“判”之通假,是都元帅府为解决两县用水争端所下的政务裁决文书。参见(金)杨丘行: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李国富、王汝雕、张宝年主编:洪洞金石录,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3页。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省判”即属
5、这类“案判”。由于目前尚未发现金朝“省判”的原件存世,关于其文书体式的研究,只能依赖大金德运图说所教录文。不过,这份录文因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摘录,故它的呈现格式与原件不可能做到一一对应。现存大金德运图说只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人修四库全书时,是否存在其他版本,已不得而知。有学者在讨论四库全书本文献时,指出四库全书所录文献可能还有其他的版本存世。参见王孝华、刘晓东:渤海德里府、德里镇与边州军镇设防问题考,中州学刊,2022年第7期。为解决上述问题,现将大金德运图说所录尚书省“省判”涉及的相关录文摘录如下:省判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面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呈检本部照得既见,钦奉圣旨教
6、商量,缘系国家德运,当慎其事。拟乞从都省依前例,选集群官再行详议,采用所长,庶得其当。(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1986年,第648册第312-313页。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的这段文字,被四库馆臣记作“省判”,因此,这份录文应当是被四库馆臣或永乐大典的编纂者认为是当时尚书都省依诏对德运一事所做“判文”的录文。此判文交代了贞祐二年(1214),宣宗授意尚书都省召集官员商讨德运集议的缘由。判文抬头书写:“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面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呈检本部照得”,(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2页。指明此事应是在贞祐二年
7、正月二十二日御前奏事时,宣宗向宰执下旨要求商讨王朝“德运”一事,尚书都省随即将皇帝旨意告知礼部,要求其查验王朝德运的讨论事宜。按大金集礼班位表奏“奏事”条载,皇帝御前听政结束后,左、右司长官从宰执处“各禀覆签所得圣旨”,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三一班位表奏,第323页。将皇帝旨意下发给六部等机构执行。此份“省判”言礼部所得的“圣旨”应是指这一在御前听政后由左司传达给礼部的皇命文书。值得注意的是,此判文虽名为“省判”,但判文的内容却并非完全取自尚书都省所做出的政务处理结果,也并非取自尚书都省向礼部等机构下发的下行文书。在这份名为“省判”的文书中,没有尚书都省如何回应礼部请求的文字记述。单就这份文书
8、的记载来看,不能断定尚书都省对礼部的提议和皇帝旨意做出了怎样的判断。此外,这种记述行文结构并不符合案判中简述事件一分析情理一提出处理意见的基本结构。谭淑娟:唐代判体文研究,第35页。加之,判文开头言“呈检本部照得“,这不仅说明都省曾向礼部递送皇帝旨意,并随之下发了要求礼部查验相应政务的下行文书,同时也说明此段文字的书写方应是礼部。其后如“自明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奉章宗敕旨,本朝德运仰商量,当时本部为事关头段,呈乞都省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同共讲议”都是以礼部自陈方式所做的对章宗朝讨论德运一事的追述。另有“省判”结尾处言,“拟乞从都省依前例,选集群官再行详议,采用所长,庶得其当”。(金)佚名:大金
9、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2、313页。其中,”拟乞从都省”显然是下级机构对尚书都省所呈上行文书的制式用语。综上,笔者认为这份“省判”所录文字,应是礼部接到尚书都省下发的皇帝要求讨论德运的政务文书后向尚书都省所上的上行文书,即后文省劄所言礼部呈的主要内容。因而,通过这份名为“省判”的文书录文,并不能厘清金朝尚书都留在处理政务所做判文的行文格式等内容。不过,永乐大典的编纂者和四库馆臣都认为此份文书是当时的“省判”。“书前为尚书省判,次为省劄”,参见(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0页。四库馆臣在大金德运图说提要中也曾言此文是“金尚书省会官集议德运所存
10、案麟之文也“,“是编所议,识见皆为偏陋,本不足录。然此事史文简略,不能具其始末,存此一帙,尚可以补学故之遗(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1、312页。四库馆臣明明知晓此份录文存在缺失,但仍将其列为“省判”。可见,在明清两代的认知中,金朝尚书都省处理政务时,书以“省判”应是一种常规之举。我们不能依此否认金朝尚书都省在处理政务时存在书写“省判”的情况。这份录文极有可能是尚书都省所做“省判”中涉及简述事件的一部分。二、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载省劄看金后期尚书都省政务指挥之文书目前,尚未发现金朝尚书省劄子的原件存世。关于其文书体式的研究,只能依赖传世碑刻和文献记载中的劄子录文及
11、相关描述。其中,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劄录文,是目前唯一一份明确被题为省劄的录文。因此,本文摘取了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劄录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这类被文献录入的政务文书,其录入之目的更注重文书承载的文字内容,行文格式上与真实的劄子存在出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还需结合金史和其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金朝尚书省劄子的基本体式与特征做一探析。希冀可以借此明晰金朝后期尚书都省指挥政务之下行文书的实况。劄子作为宰相机构指挥政务的文书形式,兴起并定型于北宋初期,且与唐宋宰相机构处理政务的发展顺势而承。李肇唐国史补载:“宰相判四方之事有堂案,处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唐)李肇撰,聂清风校注:唐国史补校
12、注卷之下,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21页在唐中后期,宰相常以堂帖等文书直接处理常规琐细政务。宋初,君主专制较之以前明显加强。因此,宰相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变小,堂帖的运用大打折扣,宰相机构转而使用劄子作为下行的指挥文书。对此,刘后滨认为,堂案与堂帖不同于需要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文书的敕牒,其是中书门下独立指挥公务的命令文书,体现了宰相对于政务的独立裁决。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增订版),第30()页。元丰改制后,王朝政令通常经尚书省行下,宰相部门传达公事的文书一般称作“省劄”或“尚书省劄子”,自后迄南宋相承不废。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
13、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在元丰改制之后的“省劄”中,“奉圣旨”与“劄付某某”等标志性用语,一应俱全。省劄在末尾日期之下注“押”,也表示尚书省宰臣签押之意。张祎:中书、尚书省札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至南宋,省劄的应用场合更为广泛,所处理的政务也远远突破事情大小的界限。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此前在唐、五代、北宋时期本应以敕处理的事情,在南宋却常以省劄来处理。此时省劄既用来批复有关官司,亦可转发制敕和赦文等重要诏书。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
14、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金朝作为唐和北宋在中国北方的继承者,其省劄是否出现了新的变化?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劄为我们研究此问题提供了线索。现将大金德运图说所收录尚书省召集此次集议的省劄中,有关文书体式的录文摘抄如下:省劄贞祐二年二月初三日,承省劄,礼部呈该:承省劄,奉圣旨,本朝德运公事教商量事,缘为事关头段,拟乞选官再行详议。尚书省相度,合准来呈。今点定下项官,须议指挥右仰就便行移逐官,不妨本职及已委勾当,同共讲究施行,不得违错,准此。(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3-314页。此份省劄将下属机构的奏呈概述于前,
15、都省的批复写于其后。这种书写格式,应用于朝廷对臣僚奏请的批复之时。这与北宋元丰以来在省劄中奏呈批复的程式化书写格式相同。这种行文格式,与元丰改制之后的宋朝省劄并无不同。张祎曾以民国贾恩线编的定县志中著录的大观三年(1109)四月的省劄碑文指出,作为元丰改制之后的北宋省劄,其所提到的“知定州梁子美劄子”,属于臣僚奏议文书的一种。这种省劄作为朝廷对于臣僚奏请的批复,通常在书写格式上,先行录入奏议文书的内容。李全德也指出,在南宋的省劄中,如果存在对奏状的批复,也会在录入的奏状之后,书写劄子所批复结果等内容。参见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第117页;李全德:从
16、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省劄并没有直接书写“奉圣旨”或与之类似的文字。“奉圣旨”仅出现于所书的礼部呈概要之中。这与两宋的省劄不同。元丰改制后,北宋和南宋所发省劄皆在开头书“奉圣旨”或“三省同奉圣旨”,以示所下政务须奏皇帝圣裁处分,秉承皇帝旨意行事。张祎:中书、尚书省劄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但大金集礼皇太子教,“大定二年五月,奉御前批劄定到护卫人从等,并奉敕旨,月给钱、粟、曲、麦皇太孙官属名称,止合依前项晋典故施行。尚书省奏劄:奉敕旨:东宫诸局分承应人,元设多少人。后来如何设到
17、许多人。写了奏知。寻送户、礼、兵三部勘到元设并在后添设到人数、根因、支破料钱等事,及随局分见合设承应人,拟到下项,准奏”。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卷八皇太子,第129页。大金集礼作为官修的会要体文献,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附录四,第517页。其所载文字仍有“奉敕旨”的程式用语。这说明在金朝此前的省劄中存在用于表示承受皇命的程式用语。因此,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劄没有使用这类承受皇命程式用语的做法,便显得尤为特别。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应与宣宗即位之初的金朝政局变化有关。宣宗本人由权臣弑君后拥立,即位之初对于宰执尤为放任。其时,张行信弹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参政奥屯忠孝平生矫伪不近人情,急于功名,诡异要誉,
18、惨刻害物,忍而不恤。诏议东海爵号,忠孝请籍没其子孙,及论特末也则云不当籍没,其偏党不公如此。无事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乃使此人与政,如社稷何!”金史卷一。四奥屯忠孝传,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435页。宣宗回以“朕初即位,当以礼进退大臣,卿语其亲知,讽之求去可也”。金史卷一。四奥屯忠孝传,第2435页。宣宗对宰执的放任可见一斑。贞祐元年(1213)十月辛亥“高琪自军中入,遂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持其首诣阙待罪。宣宗赦之,以为左副元帅,一行将士迁赏有差。顷之,拜平章政事金史卷一。六术虎高琪传,第2479页。术虎高琪诛杀胡沙虎后,继胡沙虎成为金朝当时的第一权臣。贞祐三年(1215),侯
19、挚曾上章言九事,其中第一事便是指出“省部所以总天下之纪纲,今随路宣差便宜、从宜,往往不遵条格,辄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于纪纲岂不紊乱,宜革其弊”。金史卷一C)八侯挚传,第2523页。他指明尚书都省肆意以省劄指挥六部及其他官员已成常态。不过,即便如此,如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劄的行文中仍须将皇帝的最高决策地位以引用等方式彰显。这反映出虽然宣宗初年宰执施政空间的扩大和对皇权行使的牵制,在这种情况下,在以术虎高琪为核心的尚书都省看来,准许礼部奏请以集议方式讨论德运这类的琐细政务,似乎并无奏请皇帝批准的必要。这也解释了,为何金史宣宗纪将此事记为,贞祐二年(1214)正月“命有司复议本朝德运”后便没有下文
20、。既是因为此事最终因宣宗南迁不了了之,也是因为此事的后续讨论日程和结果根本未经尚书都省呈奏皇帝知晓。如不是因大金德运图说保留了相关录文,此次讨论德运的相关事宜便被淹没于史海之中。参见(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1-320页;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第329730页。但是皇帝的最高决策地位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再有,在此份省劄中存有“尚书省相度,合准来呈”的记述,对比前文礼部所上呈文“拟乞从都省依前例,选集群官再行详议,采用所长,庶得其当”的记述,可知礼部呈文的实际对象是都省。这份呈文的批复方也是未经请旨的尚书都省。这种都留在不经皇帝圣裁而批准礼部以集议方式讨论王朝德
21、运拟案的做法说明此时省劄作为宰执独立处理政务的文书,已经可以用来独立批复有司的呈文。这与南宋出现的以省劄用来批复有关机构呈文的现象相一致。关于南宋省劄的具体应用情况,参见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此外,这份省劄结尾以“右仰就便行移逐官,不妨本职及已委勾当,同共讲究施行,不得违错,准此”(金)佚名: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48册第314页。作为付授用语,交代了交付对象。两宋以来的中书劄子、尚书省劄子除了“奉圣旨”的标志性格式用语外,还有以文末的“劄付某某”格式表示命令下达的对象。张祎:中书、尚书省劄
22、子与宋代皇权运作,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元代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书形式,称“劄付”,为明清所沿用。参见裴燕生等编著:历史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243页。这种情况在此份省劄中却未有体现,该文“行移”所表达的即“劄付”之意。不过,在金朝省劄的付授用语上,采用“劄付”字样的情况仍旧存在。如温水塔河院碑即载有“都省劄付”的文字,这说明,金朝总体还是沿用了两宋尚书省劄中的“劄付”格式和用语,只是在一些具体文书上存在差别。参见(金)佚名:温水塔河院碑,(清)李敬修:费县志卷一四下金石下,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14页a。这说明金朝省劄还可以作为一种尚书都省签发给其他机构或官员的告知
23、性文书,而并非完全意义上发布政令的下行文书。其中“就便”二字表明了这种灵活性。当省劄作为告知性文书时,未用尊称而是使用了未带感情色彩的陈述性语言“行移”。这说明自唐末北宋以来劄子代替堂帖后遗留下的临时、非正式性质的痕迹李全德:从堂帖到省札一一略论唐宋时期宰相处理政务的文书之演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2年第3期。已经消失不见。劄子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尚书都省用于指挥、通告政务的正式文书。这份省劄的特殊之处在于结尾处未见尚书都省宰执签押,这与两宋以来的省劄体例不符。按王悻中堂事记载,金末“尝闻之高土美云,其敕之全式:尚书省臊:故某官某职某人膝,奉救可追谥某名。牒至准敕。故牒年月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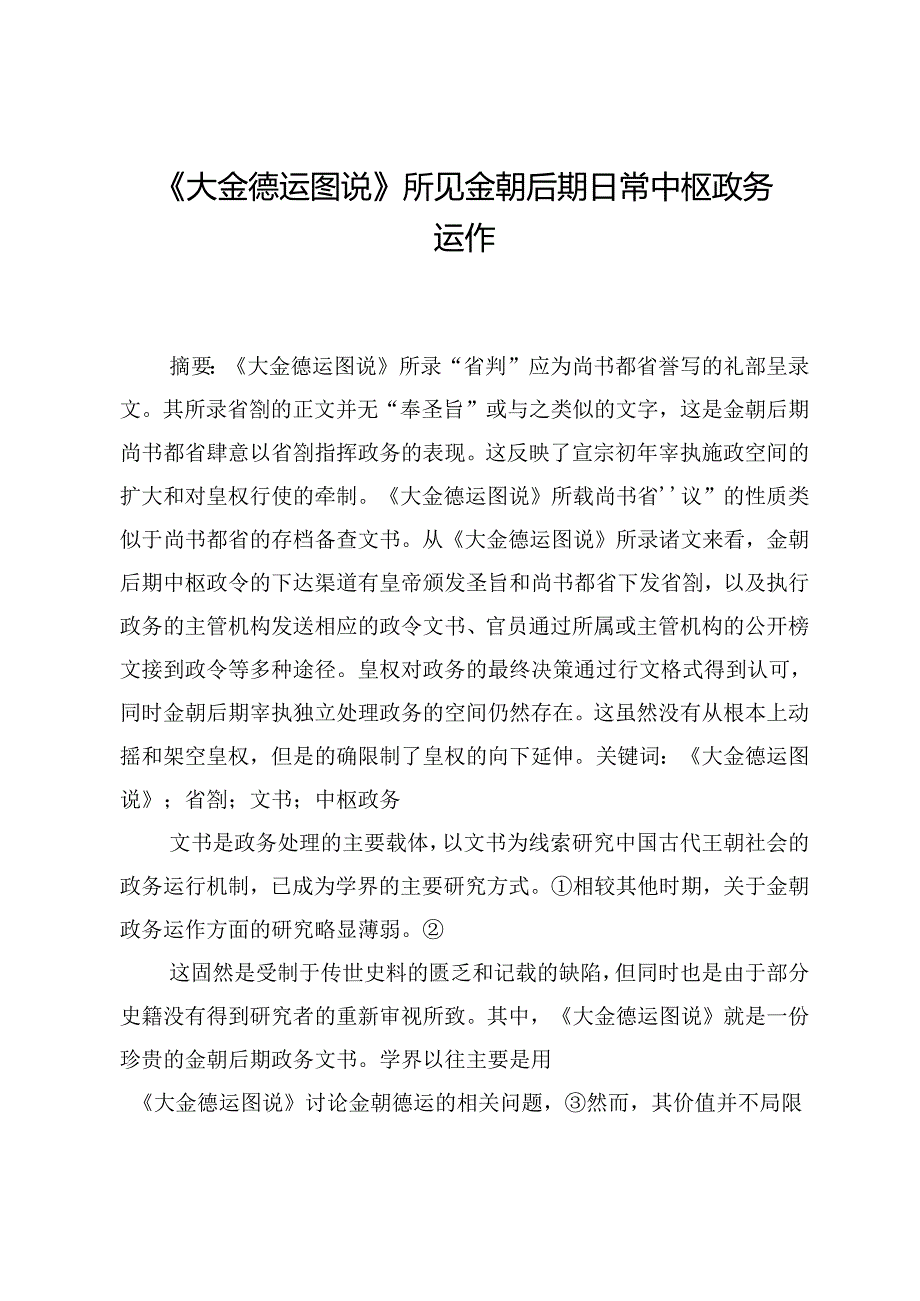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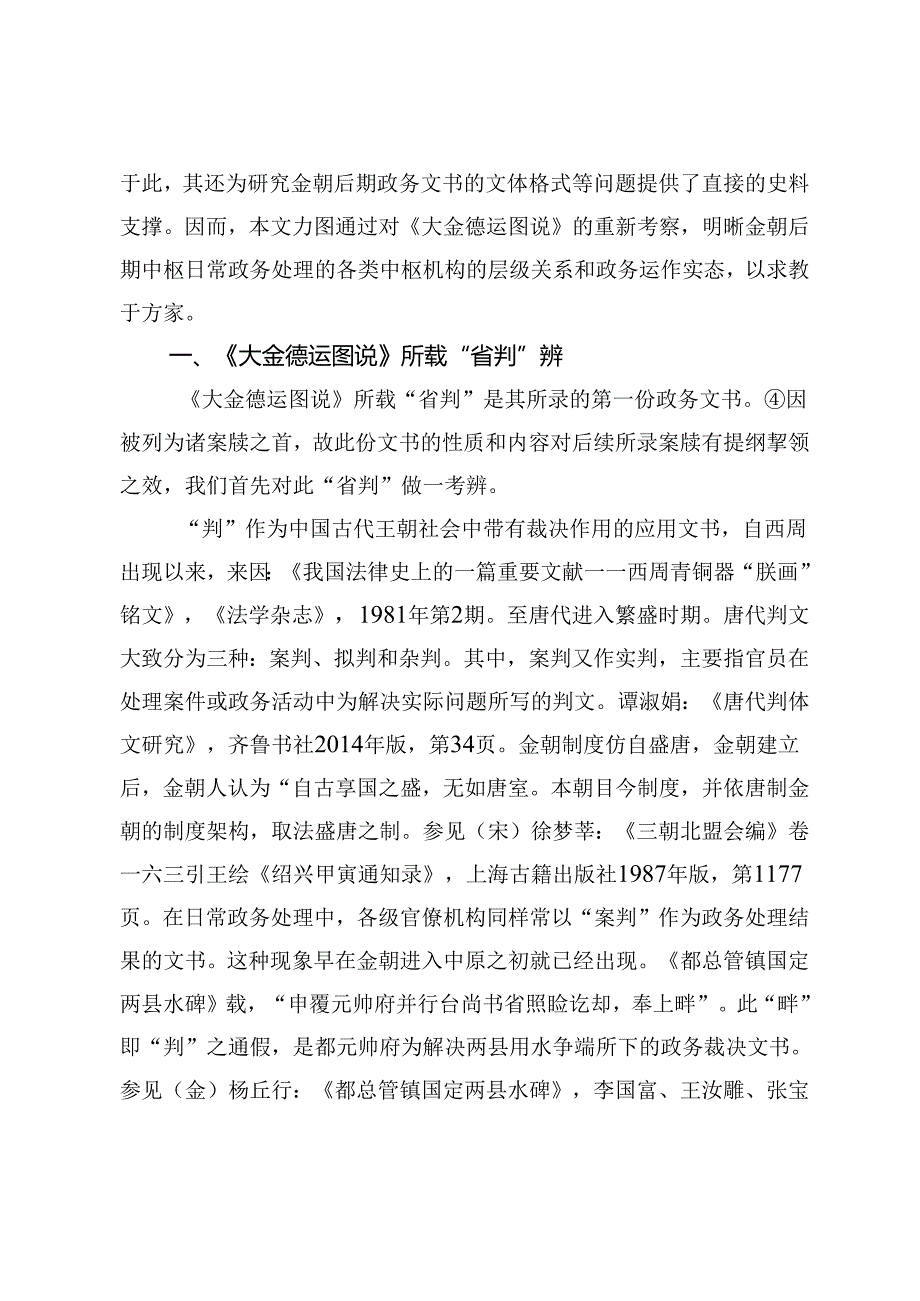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大金德运图说 大金德运 图说 金朝 后期 日常 中枢 政务 运作
 课桌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课桌文档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链接地址:https://www.desk33.com/p-1730505.html